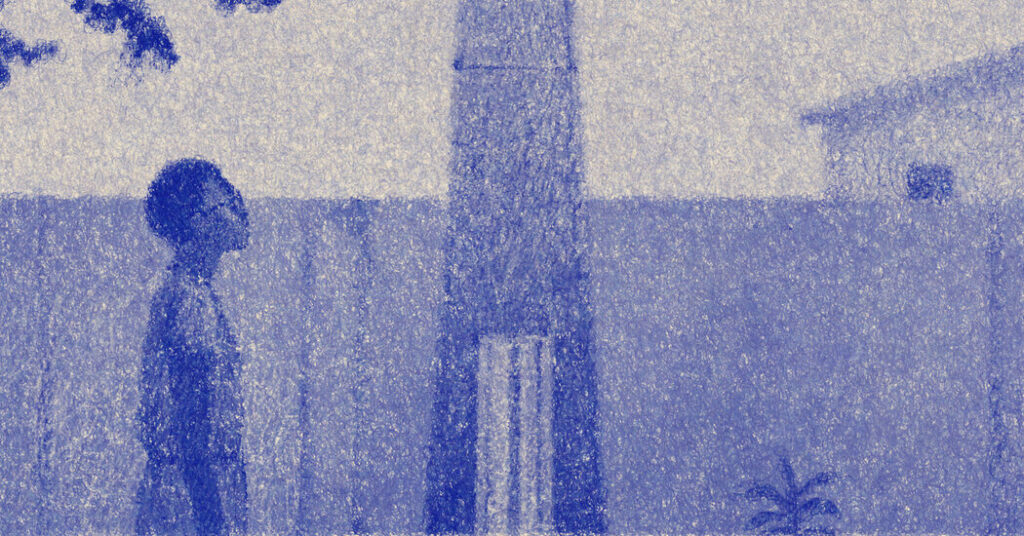去世界中心的前一晚我沒睡好。
凌晨 3 點,我發現自己在阿克拉父母家完全醒了。我的父母花了我大半輩子的時間慢慢建造這棟房子。今晚是十多年來我們第一次在加納睡在同一屋簷下。
院子裡的青蛙在呱呱叫。時差就像一條發癢的毯子一樣緊貼著我。
顯然,人們實際上無法到達這個星球的鐵心。而地球表面其實沒有「中心」。球不是這樣運作的。但是,一群形形色色的探險家和天文學家經過幾個世紀的合作,最終產生了經度,這是一條圍繞地球從北向南輻射的假想垂直線。
也就是說,實際上存在著0度經度與0度緯度相交的精確位置。世界的中心,如果你願意的話。
但與赤道(0度緯度)與南北兩極等距不同的是,0度經度沒有自然基礎。您可以將其放置在您喜歡的任何地方。人們做到了。世界各國都建立了自己的本初子午線,經常經過本國首都。格林威治是英國首都的行政區,因此格林威治子午線於 1884 年在國際上採用。
這條路線從倫敦出發,經英吉利海峽,穿越歐洲大陸,越過巴利阿里海,穿過非洲西北部,到達加納港口城市特馬,然後注入幾內亞灣。
本初子午線與赤道交會的實際點位於大西洋。但世界上距離這個水地標最近的城市是加納的特馬,我母親在那裡長大。
從我一歲起直到五歲那年夏天搬到新澤西,特馬就是我的家。在我前往加納進行為期兩週的訪問的前幾天,我在網上瀏覽並發現了那個偶然的地方。我剛剛辭掉一份艱苦的工作,對接下來的事情沒有具體的計畫。
在一次期待已久的旅行之前,你有多大可能遇到這個事實,帶著一袋給家人的禮物,並半心半意地詢問如何重建你的生活?
我在特馬的親戚並沒有接受我的熱情。 「Meridian 會修復街道嗎?」 一位表兄弟問。很公平。
我的母親以三個國家為家,她是唯一一個對此充滿熱情的人。無論是為了我自己的利益(就像當我為一個自豪地舉起一塊棉絨的幼兒歡呼時),還是因為,作為一名移民,我知道告訴別人我來自哪裡是一項微妙的任務。我仍然不知道如果是這樣的話。 用他們能理解的語言。
週日下午,我和女朋友在無情的陽光下離開阿克拉前往特馬。平時熙熙攘攘的食品攤販和避開汽車的行人的街道現在很安靜。我們先停在我姑姑家。距離我姑姑和母親長大的房子只有幾扇門。
從那裡,我們乘坐了一段可笑的短途路程(因為我母親的膝蓋不好)到了老子午線教堂,該教堂因穿過該地產的線路而得名。一路上,我們認識了一位小表弟,他留著小鬍子,身材瘦長,說話輕聲細語。雖然他的表情基本上是陰沉的,但他的笑聲卻透露出那個將繼續活在我心裡的小男孩。
在車上,我母親打電話給她的老朋友查爾斯叔叔(無親屬關係),他在教堂對面擁有一家賓館。他被指定來指導我們。
查爾斯叔叔有著友善的微笑和溫暖、令人放心的舉止,歡迎與他一起生活的房客。當他下車時,他和我母親在嘎互相打招呼。我認為嘎語對我母親來說是最有趣的語言。
她的英語很有趣,我不太懂她的其他語言,無法判斷她的機智,但我無意中聽到的關於她的大部分對話都是用Ga(她還是個女孩時這個城市的通用語言) 。我斷言它用於幾分鐘之內,它就變成了笑到肚子痛。也許這只是我媽媽的看法,但我喜歡想像世界的中心充滿了歡笑。
當我們快到教堂門口時,我們看到一個男人在警衛室裡打瞌睡。查爾斯叔叔叫醒了他,告訴他可以看到花園對面的格林威治子午線。
隨後發生了激烈的談話。保全堅稱,未經教會官員明確許可,我們不得在前方行走超過 30 英尺。他們都回家了,所以我們運氣不好。
這太荒謬了,查爾斯叔叔抗議。他無數次走過那裡,卻沒有得到這樣的許可。
警衛們也許沒有預料到會遭到任何抵抗,因此充滿了可疑的權威,並堅稱他們不會讓我們通過。
失望在我腳下蔓延。我沒想到當我觸及那片模糊的神聖土地時,我會發生轉變。但當目的地就在眼前時,一想到要被這個固執的小個子打擾,我就感到很痛苦。
沒有必要擔心。當溫和的推理失敗時,我們決定到戶外散步,穿過無障礙的花園。如果真的是嚴重違規,查爾斯叔叔就會承擔責任。警衛顯然對他的權力受到侵犯感到不滿,但不清楚除了對付我們之外他還能做什麼。
格林威治子午線以石頭跑道為標誌。外層是佈滿灰塵的磚塊,然後是棕褐色的岩石,裡面有一條細細的斑駁的紫紅色帶。它的底部矗立著一塊高尖塔形狀的白色石板,你可以想像拉鍊上方的按鈕可以打開整個世界。
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想用這小塊土地做什麼。這可能是一個冥想的時刻。想像一下,沿著這條線前進,將自己投射到幾內亞灣,在那裡與赤道交會。
我試著牢記這片土地在宇宙和文化上的無意義,以及從中提取一些意義的不可抗拒的誘惑 – 因為否則我還能怎麼做?你能在你的生活中留下印記嗎?
我媽媽堅持要我在記號筆前拍一張照片,打破了我的想法。 “不,媽媽!” 帶著成年孩子特有的熱情,我遲來地開始反抗。
她沒有被嚇倒,而是在標記腳下佔據了位置,並開始拍攝自拍影片。 “我在這裡,站在本初子午線上!” 她說。我認為我們都以自己的方式創造了意義。
或者也許不是。
表弟站在一旁,指著我們身後的教堂。
“那是什麼?” 我問他(過去式。
「我在這裡上小學,」他說。 “我的小學是教會開辦的。我不知道這條線又來了。”
他說得很清楚,沒有浮華。我從他的表情中讀不出任何訊息。
「你似乎不太在意。」我說。
他開始對我身後的空間做出真正困惑的手勢。
」不,他說。「我真的不在乎。
Emefa Addo Agaw 是《埃茲拉·克萊因秀》的前製片人,為《華盛頓郵報》和 Vox 等出版物撰稿。